首页  财政金融 财政金融  |
又要开启隐性债务置换了? |
又要开启隐性债务置换了? 谭逸鸣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 导读:2023 年初政策释放隐性债务化解信号,涉及遏制增量与化解存量,或指向金融机构推动置换,地方债试点置换隐债有空间,需关注相关风险。全文5200字,由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课题组资料整理。 摘 要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涉及哪些层面?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主要涉及两个维度: 一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自2017年以来政策端对于增量部分一直处于严格规范和约束的过程中,近期财政部回函当中亦有所明确。 二是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财政部曾明确6种存量隐性债务化解方式;在近几年的实操当中各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也基本围绕财政部六大方式来展开,与此同时还辅以加大各区域平台整合以打通区域资产负债表、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等方式统筹兼顾的缓释风险。 相关表述指向何处? 2023.1.5,财政部公布的回函里明确:“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人合理分担风险。”2023.1.8,郭主席在答记者问时阐述的是:“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率负担。” 两者表述结合起来看,2023年里,政策监管在隐性债务化解上,或指向金融机构再度推动针对于城投平台的隐性债务置换工作。 这背后凸显的便是当前压力愈发增大的财政以及地方债务问题。一方面,土地市场的颓势短期内或难以根本性扭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始终并未找到最终的化解之法。 政策还有多大空间? 关于郭主席提到的“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是否涉及发行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还有多大空间? 首先,从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角度出发: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6万亿元,扣减已批准发行的1.06万亿元后,有14.34万亿元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进行置换。而后2015-2019年,共发行置换债12.36万亿元。2020-2022年,试点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共发行1.04亿元,一方面是债务压力较大的区域进行相应缓释,另一方面是助力隐性债务清零的区域,整体规制上需要经过财政部答辩并有相对详细严密的化债计划。 另外,还可以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的空间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空间可构成可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发行规模的理论上限。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7.65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4万亿元,全国限额-余额空间为2.61万亿元。由于分省的数据暂未发布,根据估算可大致得到2022年末各省地方政府债务空间规模。 但由于地方债限额存在“收回再分配”机制,各省的限额-余额空间不完全等同于可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发行规模的实际上限。结合发行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规模来看:作为被“收回”区域的北京、广东、上海等区域发行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较多,或与经济财政实力强劲地区率先实现区域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有关;而作为被“再分配”区域的辽宁、重庆、天津、贵州等区域发行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亦较多,或与区域本身债务率偏高,政策倾向性支持有关。 风险提示:城投口径偏差;部分数据缺失所导致的偏差;宏观经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区域及平台评价的主观性。 报告目录 一、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涉及哪些层面? 二、相关表述指向何处? 三、政策还有多大空间? 四、 风险提示 2023.1.5,财政部公布了对政协委员提出《关于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提案》的答复,其中提到:"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人合理分担风险。 2023.1.8,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提及:“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率负担。 上述相关表述引发了市场对于城投相关监管动向的高度关注,推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2023年会有哪些政策空间释放?本文聚焦于以下几点:(1)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涉及哪些层面?(2) 财政部以及郭主席的相关表述可能指向何方?(3) 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一、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涉及哪些层面? 首先,我们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界定: 自2014年《新预算法》颁布后,新增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只以地方政府债券这一种形式呈现,对应的便是地方政府显性债务。 由于显性债务有着财政硬约束的规范,在逆周期稳增长的诉求下,相应的便出现了“隐性债务”这一概念。 2017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首提“隐性债务”概念:“要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2017年8月,时任财政部部长肖捷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做《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提出“严禁借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结合相关表述,大致可以将“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部分认定为“隐性债务”。 其形式识别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直接举债融资。包括“为没有收入的政府公益性项目举借的,最终由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由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等形式为企业(主要是融资平台)提供担保形成的举债融资”,“机关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为企业抵押或质押进行的举债融资”等。这类债务的举债主体主要是融资平台,对于涉嫌违规举债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政府部门出具承诺函或纳入预算决议、公益性资产抵押、财政资金偿还、用于政府公益性项目,城投平台涉及以上特征的任何一笔债务,均有可能被认定为隐性债务; (2)地方政府的中长期支出事项,主要包括政府投资基金、PPP项目、政府投资服务、专项建设基金、应付工程货物款等。与直接举债一样,并非所有的中长期支出责任都会被认定为隐性债务,主要是涉及政府固定支出责任的部分可能会被认定为隐性债务,比如承诺本金回购、承诺最低收益、承诺承担社会资本方资本金损失等;而完全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项目支出,并不会被认定为隐性债务。 进一步来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主要涉及两个维度: 一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自2017年以来政策端对于增量部分一直处于严格规范和约束的过程中,近期财政部回函当中亦有所明确。 二是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财政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中明确6种存量隐性债务化解方式: (1)安排年度预算资金、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偿还;(2)出让政府股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3)利用项目结转、经营性收入偿还;(4)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5)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偿还;(6)采用破产重整或清算方式化解。 而在近几年的实操当中各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也基本围绕财政部六大方式来展开,与此同时还辅以加大各区域平台整合以打通区域资产负债表、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等方式统筹兼顾的缓释风险。 而在存量债务化解当中,金融机构参与存量隐性债务化解,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从而以时间换空间,自2018年的中发27号文以来,至后面的国办发101号文、国办发40号文、33号文以及银保监45号文均有所阐述。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的逻辑框架和实现路径都很清晰,但站在当下节点,年初提纲挈领的再提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指向何处,政策空间有多大? 二、相关表述指向何处? 我们先来仔细品读财政部回函以及郭主席相关表述: 财政部回函里面明确的是:“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人合理分担风险。” 郭主席在答记者问时阐述的是:“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率负担。” 两者表述结合起来看,2023年里,政策监管在隐性债务化解上,或指向金融机构再度推动针对于城投平台的隐性债务置换工作,彼时2019-2020年全国各地实施落地的较多,很大程度上为城投平台债务化解创造了不小的空间,这也是十年隐债化解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其在优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成本负担上起到了关键的腾挪作用。 这背后凸显的便是当前压力愈发增大的财政以及地方债务问题,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土地财政压力愈发增大,尽管地产政策有明显转向,但短期内或难以根本性扭转土地市场的颓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始终并未找到最终的化解之法,尽管关于隐性债务并没有公开全面的数据样本,但观察城投有息债务的增长便能感受到压力仍存,并且从财政部长相关表述也可以印证。 2021年6月7日,刘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20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得到缓释”。这里的措辞仅仅是“缓释”。 从这几年城投的融资性现金流以及债务期限结构的演绎可以看出,2019-2020年当中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城投平台融资性现金流改善非常显著,且债务期限结构有所拉长。 但在这两年隐债置换的微观实操当中,确存在各种化债不实的现象,应运而生的便是2021年的银保监15号文以及各场所收紧规范发债,故而在2021-2022年当中隐性债务置换工作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对应看城投融资性现金流和债务期限结构、品种结构的改善也失去了金融机构加大隐性债务置换这一着力点。 而站在2023年初展望,城投平台的债务压力仍在不断提升当中,除了财政约束之下平台内部现金流承压之外,理财行为变化之下也会对债券净融资产生一定影响,故而政策端给出进一步的空间予以缓释非常关键,进一步结合财政部、人民银行以及银保监相关的措辞表述来看,年内进一步大力推动隐性债务置换工作值得关注,但前提仍然是规范化和市场化,正如落实“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金融风险管理能力”这一表述,从微观视角观察来看,可能存在着不小的约束。 进一步而言,市场会关注政策还有哪些空间,关于郭主席提到的“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是否涉及发行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 三、政策还有多大空间? 当然,郭主席答记者问当中提到的“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相关表述是在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这一提纲挈领的表述之下的,更多或是指向金融机构加大隐性债务置换工作,毕竟地方政府债券更多还是在财政口的管辖之下,但我们来算一算,地方债试点置换隐性债务还有多大空间? 首先,从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角度出发:首先,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说明》,“201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加上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0.6万亿元,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6万亿元。对债务余额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的存量债务,通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由地方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即扣减已批准发行的1.06万亿元后,有14.34万亿元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进行置换。而后2015-2019年,共发行置换债12.36万亿元。 2020-2022年,试点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共发行1.04亿元,一方面是债务压力较大的区域进行相应缓释,另一方面是助力隐性债务清零的区域,整体规制上需要经过财政部答辩并有相对详细严密的化债计划。 从拿到试点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的区域公开披露来看,2020及2021年试点建制县拿到了规模不小的再融资债置换隐债,一定程度上对区域债务压力缓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另外,还可以从全国各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的空间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空间可构成可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发行规模的理论上限。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7.65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4万亿元(截至2022年11月末),全国限额-余额空间大致为2.61万亿元。 分省份来看,由于分省的数据暂未发布,我们以2021年限额+2022年公告新增限额的估算2022年各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再以2021年末债务余额+2022年新增地方债估算2022年末各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大致得到各省的地方政府债务空间规模。 根据估算情况,上海、江苏、广东、河南、北京等省市的限额-余额空间相对较为充足。 但由于地方债限额存在“收回再分配”机制,各省的限额-余额空间不完全等同于可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发行规模的实际上限。 观察区域“收回再分配”情况可发现,被“收回”区域往往是限额-余额空间较充裕的区域(如北京、上海、广东),被“再分配”区域往往是限额-余额空间较窄的区域(如新疆、贵州、重庆、湖南、天津)。 再结合发行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规模来看:作为被“收回”区域的北京、广东、上海等区域发行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较多,或与经济财政实力强劲地区率先实现区域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有关;而作为被“再分配”区域的辽宁、重庆、天津、贵州等区域发行置换隐债的再融资债亦较多,或与区域本身债务率偏高,政策倾向性支持有关。 四、风险提示 1.城投口径偏差。本文所采用的城投口径系非传统产业类的广义城投口径,较传统意义上的城投,口径更为广泛。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2.部分数据缺失所导致的偏差。由于部分城投公司历年年报数据缺失,或会导致相关指标计算有偏差。 3.宏观经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区域及平台评价的主观性。债务风险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宏观经济下行或导致各地偿债压力超预期抬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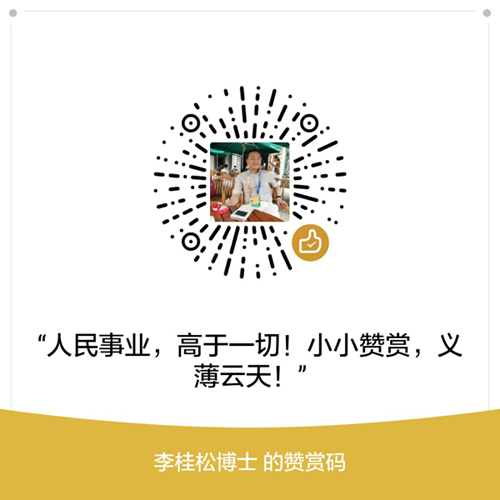 |
|||
2025-5-2 1044 1044
|
|||
|
|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17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178号